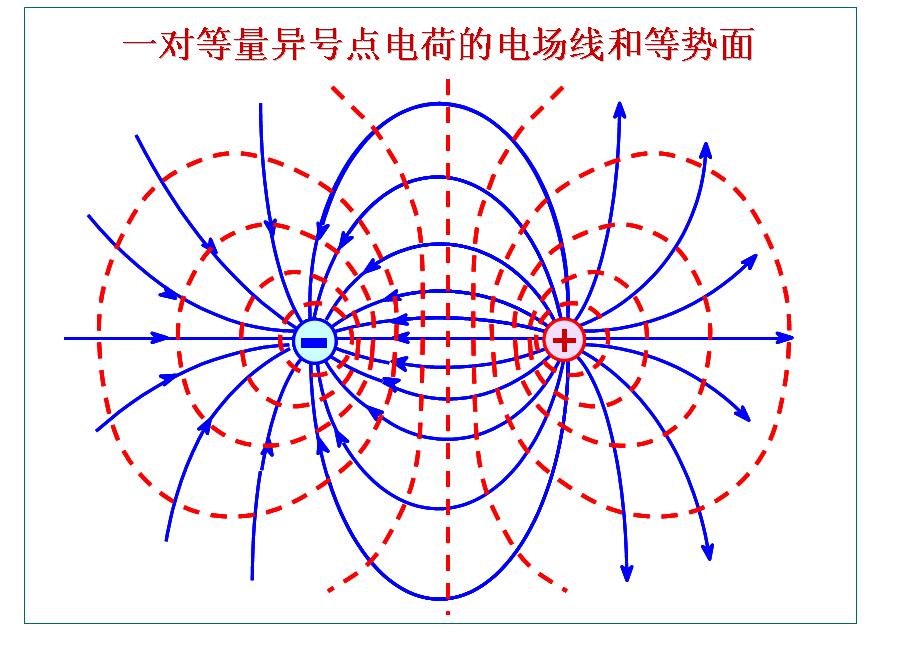爬上府谷县城西北角的五虎山的山顶,终于见到了被人们称之为陕北民歌活化石的柴根老人。今年88岁的柴根老人,身体依然硬朗网赚项目,精神依然清爽。几句简单的寒暄过后,我单刀直入地说明了来意:想听他老人家唱几首陕北民歌。老人倒也爽快脚夫调是哪里的民歌,欣然答应,一连给我唱了好几首民歌。歇息期间,我不失时机地向老人了解他年轻时有关赶牲灵的一些情况。说起赶牲灵,老人一时来了精神,说他从十几岁就开始赶牲灵,一直赶到解放后供销合作社时期。柴根老人说,他赶牲灵经常走四个四百八(大约是四百八十华里):第一个“四百八”是从府谷经神木到榆林,第二个“四百八”是从府谷经东胜到包头,第三个“四百八”是从府谷经河曲到呼和浩特,第四个“四百八”是从府谷经保德到太原。一个来回或半月或二十天不等,一路上风吹日晒,山高沟深,劳累艰辛,可谓是一言难尽。我问老人,那你为啥不安安稳稳待在家里,何必要劳神费心去赶牲灵呢?老人的回答只有四个字:活命,自由。他说,出外赶牲灵比家里种地挣得多;再说了,赶牲灵的路上,你想走就走想歇就歇,想吼就吼想唱就唱。待在家里种地,整天围着屁股大的一点地方转,一点也不自由。
说到赶牲灵,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脚户们在路上有没有个相好的?对于这个问题,柴根老人的回答是毫不含糊的:有。要是没有,一路上孤单寂寞,你怎么能熬得过?
又问:你路上有相好的,那你老婆就不管你?
回答:毛主席都管不了我,她能管得了我?
柴根老人的回答看似有点直白朴实,其实他的话中隐约道出了陕北人赶牲灵的根本原由:一是生活所迫,二是对自由的渴望,三是割舍不下“你若是我的哥哥哟招一招手”的那份依依惜别的爱。其实,这也正是陕北民歌的本质所在。
仔细审听柴根老人演唱的《赶牲灵》,你会明显地感受到,歌中的字里行间渗透着一股只有那些饱经沧桑的人才独有的那份荒凉、古朴、沙哑和绝望。
毛驴驴不乖那圪棒棒捶
挨打受气那因为了谁
毛驴驴叫唤有啥错
红火个两天我步上走呀
石狮子长腿不上树
想老命想得那实在不行
骑上骡骡八匝坡坡瞭
心也跟上你走了
骑骡骡骑在马身上
种病种在你身上
想老命想得上不了炕
炕塄上画下那人模样
想老命想得得了病
抽签打卦问神神
心里头想老命井里头看
眼里头泪蛋蛋抛也抛不完
再封闭的农业经济也离不开货物的运输和商品的交流。旧时,陕北是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封闭型的农业经济,然而,陕北人仍然需要有人把本地的土特产卖出去脚夫调是哪里的民歌,再从外地把自己需要的日用品买回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赶牲灵的便运用而生。在陕北特殊的地理环境下,千百年来,运货驮人以及货物流通,终年由这些赶牲灵的来承担。他们或吆上毛驴或赶上骡子或拉上骆驼,风餐露宿、风雨无阻,出神府进蒙地,下延安入关中,走三边去宁夏,过黄河到山西,把陕北的红枣、绿豆、羊皮等土特产运到外地,再把外地的洋布、食盐、烟叶等换回陕北。
赶牲灵的每天的行程(也称每站)大约是七十华里左右,有时为了赶路程或者是急着要见到心中的那个妹妹,也有每天走八十里九十里甚至是一百里的,这叫“放大站”。民歌中对此多有反映,比如:“马铃子响来鞭子抽,记起我情人放大站。三站改成走两站,赶死赶活为了谁?”赶牲灵的汉子们离家外出少则七天八天,多则一月两月,山高路远,地僻人稀,存留在他们心中唯有的一点温存也许就是每天晚上能够给他们提供吃住甚至是爱的途中那一家骡马店了。是呀,有赶牲灵的就有开店的,赶牲灵的把开店的看成是土地爷,开店的则把赶牲灵的当作是财神爷。一来二往,人熟了,情生了,凄美而浪漫的民歌与爱情故事便随之流传开来了:“你赶上骡子我开上店,来来往往常见面。大路畔上铃子响,刘成和哥哥过来了。”“四十里长涧羊羔山,好婆姨出在张家畔。张家畔起身刘家峁站,峁底里下去我把朋友看。”
对于许多赶牲灵的来说,浪漫与温馨只不过是如流星般的好梦易逝,而劳苦与艰险却似噩梦般如影相随。一路上,他们遇到的最大的危险,一是黑风,二是土匪。黑风会让他们迷失方向、忍饥挨饿甚至是葬身沙海;遇上土匪,轻者遭越货,重者遭杀头。前者是天灾,后者是人祸,这天灾人祸时时处处都在威胁着赶牲灵者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他们才会脚踩大地面对苍天发出这样的诘问:“三月的太阳红又红,为什么我们赶脚的人儿这样苦命?”
许多人对赶牲灵这一现象可以说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谓的其二,就是有关赶牲灵的一些基本常识。赶牲灵、赶牲灵,牲灵者,可以是毛驴也可以是骡子亦可以是骆驼。吆毛驴赶骡子多走山路且晓行夜宿,而拉骆驼则多走沙地,且夜行晓宿。
还有民歌《赶牲灵》里常唱的那句歌:“走头头那骡子三盏盏灯”这里边提到了两个概念,一是“走头头骡子”。赶牲灵很少是一人一骡去赶,一般都是几人几骡或十几人十几骡组成一支赶牲灵的队伍。在赶牲灵的队伍中,走在最前头的那头骡子就是走头头骡子。走头头骡子不但要强壮而且要机灵,赶走头头骡子的人大都是那些长年经营此道,且经验丰富的脚夫。故而,赶头骡的人的工钱也比其他人的多一倍。二是“三盏盏灯”。只有走头头骡子才能戴三盏盏灯,三盏盏灯就是在骡子笼套顶部两耳之间用铜丝竖扎几根红缨缨,下端裹着三面铜镜,阳光一照闪闪发光,如三盏灯。三盏盏灯一是起装饰作用,二是起信号作用——当两支赶牲灵的队伍相遇时,只要灯光一闪,双方便都意识到,对面来了赶牲灵的,以便及时避让,以免狭路相逢。
赶牲灵也免不了要缴税,这就又涉及到了一个特殊的概念——骡柜。据《绥德县志》记载:1925年前后,绥德县衙和当地的反动军队、土豪劣绅串通一气,组织了“骡柜”,敲诈勒索脚户,大路上遇见脚户,骡柜的人不但要向他们征税,而且还强迫他们给军政人员无代价地去支差,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如不去就得挨打挨骂。
赶牲灵的这一行当,到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演变成了拉架子车和拉牛车。那时的脚户也由为私人运货转为给县城的供销合作社运货。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陕北大地人民公社化后,黄土高原上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便渐渐地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陕北,有关赶牲灵的民歌无以数计,可以说哪里有“赶牲灵”的哪里就有民歌《赶牲灵》。
我叫你家里务庄农
你一心想起个赶牲灵
哥哥赶牲灵一十八年
自幼没走过瓦窑堡店(志丹民歌)
我吆上骡子你开上店
来来回回常见面
三疙瘩石头两疙瘩砖
多会儿回到本乡田 (延长民歌)
人人价都说赶牲灵好
我把那牲灵赶够了
砂锅熬起半锅锅肉
想起家里难糊口 (横山民歌)
生来一十九赶牲口
迭马头远走山西一个州
路过要走绥德州
周家硷的果馅入口一个酥 (甘泉民歌)
人家男人搞买卖
我家男人赶牲灵
赶上毛驴刚三岁呀
一心要走个定边城(清涧民歌)
由《赶牲灵》衍生出来的民歌还有《脚户调》《脚夫调》《赶牲口》《赶骡子》《拉骆驼》《驮盐调》《刮野鬼》等。
当然,在众多的民歌《赶牲灵》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远,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是以下这一首:
走头头那个骡子哟三盏盏那个灯
带上的那上铃子哟哇哇的那个声
白脖子的那个哈巴哟朝南那个咬
赶牲灵的那个人儿哟过呀来了
你若是我的哥哥招一招手
你不是我的哥哥哟走你的那个路
毫无疑问,这首《赶牲灵》作者是张天恩。出生于吴堡张家墕村的张天恩,从小因家境贫困便随父亲一起赶牲灵,走三边、上草地、过黄河、下南路,从事运输货物和贩卖牲口的行当。虽目不识丁,但见多识广,朋友众多。张天恩在漫长而孤独的赶牲灵的路上,走一路唱一路。赶牲灵的人都愿意与他结伴,他们知道,哪里有张天恩,哪里就红火热闹,张天恩的名声也随之一天天地大了起来。赶牲灵所到之处,一听到他的歌声,人们就知道张天恩来了,每到一处便有好多人围观,不唱几首陕北民歌就走不了。
《赶牲灵》这首民歌是张天恩1945年春天编出来的。那天,大门墩上蹲着一只白脖子哈巴狗,这只哈巴狗是张天恩从山西柳林给王震买回来的。当时,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文工团的演员就住在绥德义合镇的一家骡马店里。有一个演员叫杜锦玉,是米脂中学的学生,曾演过《兄妹开荒》和《白毛女》,在边区名气很大。文工团里还有一个音乐家叫王元方,他和杜锦玉一直在默默地相爱着。那天早晨,张天恩吆着他的骡子就要离开义合到绥德开会,王元方也跟他们一起回绥德。骡队的人马起身了,头戴三颗镶镜绣球的走头骡子走开了,蹲在大门墩上的白脖子哈巴狗朝南咬开了,哇哇的串铃响开了。王元方和杜锦玉是频频挥手,恋恋不舍。目睹此情此景,张天恩突然来了灵感,随口吟出这首民歌——《赶牲灵》。
《赶牲灵》一经传唱,很快就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陕北民歌中的经典之作。张天恩一生创作了近百首陕北民歌,文化部命名其为“民间艺术天才”,2007年,吴堡县将张天恩和他的民歌《赶牲灵》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
陕北民歌的文学化和影视化,是陕北民歌走向产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笔者早就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将民歌《赶牲灵》创作为小说或改编为电视剧。要创作小说或电视剧,那就必须了解和熟悉赶牲灵的人物命运。据资料显示和实地调查,赶牲灵的人大都生活艰苦,命运坎坷,他们吆了一辈子牲口,最后还是穷困潦倒,终其一生。
比如柴根,四十多年的脚夫生涯、骡马牲灵,荒漠古道、店家女人,虽然一生经历了太多,但留给这位八十多岁老人身后的仍然是他一生不能改变的农民的身份。
还有张天恩,虽被人们誉为“民间艺术天才”,“民歌大师”,也曾被请到西北艺术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当过老师。可惜他撂不下生他养他的黄土地,撂不下他情有独钟、赖以生存的牲灵,他当了三年民歌老师后又回到了老家,继续他的老本行。结果还是因为赶牲灵,他背上“投机倒把”的罪名被判了三年徒刑,出狱后还是因为赶牲灵走上了自己的不归路。1970年农历9月初9,张天恩在贫困交加的赶牲灵的途中,病逝于山西柳林县的灰塌子村。
因编唱《脚夫调》而出名的李治文,从十来岁的时候就跟上他的爷爷走三边、卖菜籽,并将自己在赶牲灵的路上与郝滩村赵家骡马店的店家女子的爱情悲剧用血和泪向人们倾诉了出来:“四十里长涧羊羔山,好婆姨出在张家畔……不唱山曲我不好盛,唱起了山曲我想亲人。你走东来我走西,无定河让咱们两分离。”李治文一生最辉煌的一件事就是1954年曾到北京的怀仁堂给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唱过《赶牲灵》,之后,同样是因为恋土恋家恋人,他先后离开了中央歌舞团陕北民歌合唱团、延安歌舞团,回到了他的老家绥德,当上了本本分分的农民。
还有府谷的陕北民歌歌王王向荣,吴堡张天恩的同伴张生枝……还有太多太多的曾经跋涉陕北高山深沟、荒漠古道的赶牲灵的汉子们,他们一生的命运又是如何呢?艰难的生存环境,保守的农民意识,恋土恋家恋歌的生命情结,使他们很少有人能够走出这块黄土地,黄土地上的丘陵、大漠、草滩……
艺术可以高于生活,但却必须尊重生活。追寻赶牲灵者的生活轨迹,深谙赶牲灵者的人生命运,表现赶牲灵者的思想情感,是每一个试图将《赶牲灵》文学化和影视化的艺术创作者必须把握好的一条艺术命脉。